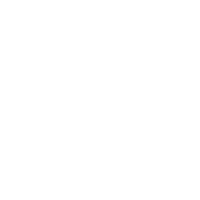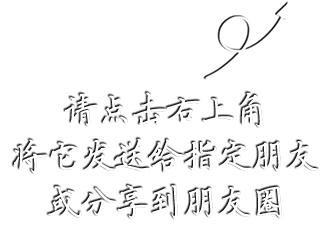父亲节记事
今日高密
2024年06月18日
◎张泽森
画 ◎夏硕男
终于空闲出一个周末,得以有时间准备学校的手抄报比赛。这次不打算画黑白的了,因为总觉得阅读是很有生气的一项活动,黑白总显得太沉闷了些。于是让母亲从家里把之前用过的马克笔寄了过来。打开快递的一刹那,看着熟悉的黑色笔袋,仿佛又回到了幼时拎着它去上美术课时既期待又不情愿的心情。
在幼儿园展露出画画的兴趣后,升入一年级,母亲就给我报了绘画兴趣班。我还记得那天,母亲牵着我走进画室。画室就在我家楼下,方便我自己去上课。上课后画的第一幅画,我也清晰地记得,是一家三口晨起刷牙的情景,校长看后对老师问道:“这是她自己画的么?”老师点点头。一点点星光在我心中升起,那是被认可的喜悦。之后,那幅画被印在了画室招生的小册子上。六年级时,由于升学的压力,结束了在画室的课程。但我和绘画的缘分未尽,升入初中,班级的黑板报被我承包,在各项绘画比赛中崭露头角,总之,关于绘画的一切,几乎都有我的身影。直到现在都是如此。那点点星光,历经多年,仍在我心中闪耀。
为什么说既期待又不情愿呢?因为兴趣是兴趣,当兴趣变成了一项你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时,意义就变了。在画室的最后一年,我几乎不愿意去上课。爱玩是小孩子的天性,本来一周只有两天的假期,还要花一天去上课。再加之有了手机,对绘画的兴趣也就减弱了些。但每当画完一幅画,那种成就感是任何东西都无法取代的。“没有一个艺术家不爱自己的缪斯”,在画室画下的画,至今还保存在家中。闲时翻出来看,当年画下它们的场景如在眼前。
手抄报的线稿画好,准备上色时,拉开了装有马克笔的黑色笔袋。昔日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友依然在,上百支笔仍然完好地保存在袋中,我好像听见它们在和我打招呼:“嗨,老朋友,我们又见面了。”只是它们中的一些蒙上了灰尘,且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有好些已经干涩了,我的老朋友们终究是“老”了。手抄报画得也并不顺利,许久未动笔,自然是生疏的。且我把它当作了必须要完成的任务,并非兴趣。怀揣着绘画兴趣的小小少年,也许早已消失在身后。担负着任务的我,还要坚持走下去。
只是画好后的手抄报我竟有些不愿意去看它,因为它与我想象中的实在“大相径庭”,我的画艺竟退步至此了么?还是我从一开始就未倾注心意进去,所以画出来的也不尽人意?画它时,我只是想着是否能拿奖、能否讨得评委老师喜欢,再也没有幼时只想画出心中所念的纯粹。有些东西,在成长过程中必须舍去,但这颗纯粹之心,我却想持久拥有。回想这一路走来,我失去了许多,得到的却也不少。绘画带给我美的启迪,使我受用一生。当年对于绘画的舍弃,又何尝不是成就了现在的我。
那些热爱画画的小小少年啊,请你继续怀揣你的兴趣,步履不停地走下去;担负任务的今日之我,也坚信“道阻且长,行则将至”呢。毕竟没有什么年少不可得之物,我亦不会受困于此。
要坚信,一路坚持下去,我们想要的,都会有。
父亲节这天,我拒绝了约我去钓鱼的朋友,推掉了同学聚会的酒席,和老婆孩子一起回老家过节。我们给父亲买了一件夹克衫和一件衬衣,又买了猪头肉、小龙虾、花生米等父亲喜欢的酒肴,还买了一箱啤酒,准备回家好好孝顺一下老人。
其实,我住的小城离老家不到100里路,开车不用一个小时就到了,但平日里许多繁杂事务,加上我比较懒散,很少回家。
沿途是金黄的麦田,田野里大型收割机在轰鸣着割小麦,农民们在田间地头等着丰收的果实。这美景,对于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忙得晕头转向的人来说,真的“很治愈”。
现在割小麦已经不再用镰刀,收割机割完,直接把麦粒送到家里,省去了运输、晾晒、打场、扬场等诸多环节,用父亲的话说就是,现在种地就跟耍似的,可轻松了。所以,自从老家用上了收割机,每年的麦收,父母都不让我回家帮忙。
驾着汽车,吹着口哨,不一会就到家了。家里大门紧闭,铁锁牢牢把在门上,父母一定是去了田间。为了给父母一个惊喜,我们回家的事没有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从门缝里往里看了看,院子里杏树上的杏子已经变黄,房檐下堆着刚收获的麦粒。我掏出电话打给父亲,可是电话没人接听。幸亏邻居的王奶奶听见动静走了出来,从她那里我们知道,父母早晨四点就去地里浇刚种上的夏玉米了。我以前在家干过农活,懂得“三秋不如一夏忙”的道理。麦收又叫“双抢”,也就是抢收抢种。记得父亲说过,“麦熟一晌虎口夺粮”,如果不抓紧时间,晚割一个时辰,就可能因为天气原因让全年努力付之东流,所以抢收就是抢馒头,是虎口夺粮。再就是抢种,麦收以后就要种夏季玉米,夏玉米生长周期一定,如果种得晚了,不光减产,还会影响下季小麦的播种时间,所以叫抢种。记得父亲说过,晚收十天不如早种一日。
这样想着,就来到了地边,母亲拿着水管子在喷水,父亲在拖拽整理水管,两人的身上都沾满泥水,他们可能过于专注,所以并没有发现我们。儿子从车上下来,跑着奔向田里的老人,一边跑一边喊着爷爷奶奶,父亲发现了跑向他的孙子,挓挲着两只泥手想拥抱孩子,却又怕给孩子弄一身泥水,儿子不嫌弃,一下子抱住了他。父亲很高兴,爬满络腮胡子的脸红红的,不知是被太阳晒的,还是看到孩子高兴的。他用满是泥水的手指在孩子的脸上点了几下,孩子立刻变成了“大花脸”。母亲见了,一边埋怨父亲,一边喊孙子赶紧过去把脸洗干净。孩子洗完脸,就要夺奶奶的水管子,他要浇地,母亲嘴里说着不要弄脏衣服,就把水管子给了孩子,孩子拤着喷水的管子,高兴地大喊大叫,一不小心,雪白的运动鞋就陷进了泥里,他干脆脱掉鞋子,赤着脚继续喷水,还一边喷一边喊着:“下大雨啦!”母亲看着孩子的高兴劲,脸笑成一朵菊花。
妻子是城里的姑娘,每次回来都是在家里,这次来到田里很不适应,那高跟鞋因为水土不服,歪三斜扭不听使唤。脸上的防晒霜被汗水冲得沟壑纵横,这样的温度不知是否和桑拿房里的感觉一样。父亲一见,赶紧从孙子手里接过水管,让母亲领着孩子和妻子一起回家做饭。
孩子显然还没玩够,但母亲害怕火登登的太阳晒黑了她的宝贝孙子,硬是把他拽走了。父亲接替了母亲的工作,我接替父亲拖拉水管。开始父亲让我也回家,看到我非要留下不可,就不再坚持。我把一支烟点燃,送到父亲口中,父亲一口吸去了半截,说:“光忙着浇地了,一上午也没顾得吸口烟。”他含着剩下的纸烟,双手抱着水管在烈日下站着,头顶上头发已经褪净,光滑的头顶泛着金光。老人家的身子明显没有先前挺拔,是啊,已经七十岁的人了,在城里,七十岁的老人已经退休十年了,他们每天除了跳广场舞,就是打扑克、钓鱼、遛鸟。可是七十岁的父母还种着八亩地,尽管父亲说现在种地累不着,但面朝黄土背朝天还是他们的写照。
拖水管的活不累,但由于气温很高,井水冰凉,水管上凝聚了水蒸气,湿漉漉的,弄得两只手上都是泥水。气温越来越高,太阳越来越亮,汗水迷糊了我的眼睛,用手擦拭,弄得满脸泥浆。父亲看到我的狼狈样,就让我过去洗脸,并再次让我回家,可我是来陪父亲过节的,怎能撂下父亲一人干活自己当逃兵。
终于,母亲骑着电动车带着儿子来送饭了。我让父亲停下机子吃饭,再休息一会,但父亲说人歇机子不能停,下面还有好几个人等着用机井,今天必须把这块地浇完。母亲从父亲手里接过水管接着浇地,说她在家里已经吃过了,让我和父亲到地头树荫下吃饭。
儿子早就在那里铺好塑料布,向着我们两个喊叫:“野餐开始了。”塑料布上,摆着一方便袋猪头肉、一方便袋花生米、半碗酱腌咸菜、几瓶啤酒和雪白的馒头。我们席地而坐,我把啤酒瓶盖打开,递给父亲一瓶,儿子从电动车上拿来一瓶可乐,就开始了我们的“野餐”。
儿子把他的可乐瓶子和他爷爷的酒瓶子碰了一下说:“祝爷爷节日快乐。”父亲拿着酒瓶,疑惑地问:“今天是什么节?”“父亲节啊,每年6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就是父亲节。而每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天是母亲节。”儿子背书似地向他的爷爷卖弄。父亲听了,夸赞儿子懂事多,接着自言自语说:“今天这节,明天那节的,都是因为日子好过了。这就是老一辈理想中的‘天天生日,月月年,变着法儿吃好饭。’”说完,一仰脖子把半瓶啤酒喝了下去。我赶紧把烧肉往他眼前挪了挪,父亲却拿了一块咸菜丢进嘴里,说:“流了一上午汗水,还是咸菜过瘾。”
儿子耐不住寂寞,早就到他奶奶那里去玩水了,看着父亲几口喝干了瓶中的酒,就要给他再开一瓶。父亲摁住我的手说:“不喝了,你下午还要回去,我和你娘浇完地还要把水泵拉回家,酒要闲的时候再喝。”说完拿起馒头,大口吃了起来。父亲咽下一口馒头:“你们没事就别往家跑,我和你娘身体都很好,前些日子上级来给65岁以上的老人体检,我们除了血压有点高,一切正常。开着车一来一回,不用喝油?”我还没有说话,父亲继续说:“今后回家也不要买东西,现在日子好了,吃穿不愁。你们给我买的衣服我都看不中。你说我穿着白衬衣、黑皮鞋在这里浇地,狗也笑掉大牙了。你以为我是公社干部?真有那孝心,领着孙子回来,比买什么都好。”
吃完饭,父亲看看手机,说:“快三点了,让你娘拉着你们回家,准备准备赶紧回城吧。”
父亲走到专注喷水的儿子跟前,用他长满胡子的脸,在儿子脸上蹭了一下,没有防备的儿子,吓了一跳,看到是爷爷的恶作剧,一边说着爷爷坏,一边向爷爷喷水。父亲抢过水管,说“臭小子,滚回城里去吧,记得过年给老子拿回一张大奖状。”
在回去的路上,看着后备箱装不下放到座椅上的黄瓜、小葱、杏子,我的眼眶有点发热。父母都是七十多岁的人了,我们真应该像歌里唱的那样“常回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