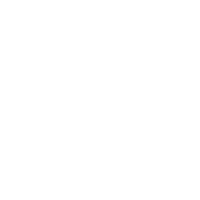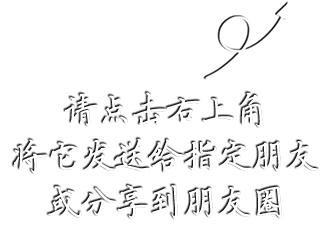母亲的文化
今日高密
2024年09月13日
◎岳桂荣
母亲的爷爷是私塾先生。每天割完猪草回家后的母亲,来不及摘掉头发上的青草,就小跑着奔向村后头太姥爷的私塾教室。温暖的阳光亲吻着母亲贴在后背黑黑的马尾辫。很快,母亲的鼻尖就亲吻上了太姥爷私塾教室白色的窗纸,踮起的脚尖儿勾到了教室内翻书的声音,轻巧的风儿透过细细的窗缝和薄薄的窗户纸,把教室内并不整齐的读书声衔到母亲耳畔: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扁担槐木解,油筐草绳拴。
太姥爷了解母亲的心思,但总是说:你不用着急,大大再上就中。偶尔,太姥爷会在家教母亲认识一些字,一个个黄豆大小的字是母亲最喜欢闻的味道。1947年,太姥爷被列为斗争对象,4周岁的私塾在6周岁母亲的望眼欲穿中提前完成使命。
外公患心脏疾患,外婆小脚不能出门,作为家中长女的母亲早早承担起家庭重担。她给自己下达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全身心供应舅舅考学。家里的牛羊鹅鸡兔跟着她的脚印不停地转,田里的玉米棉花小麦喜欢低头抚摸她小小的脸蛋和胖乎乎的小手,村南头常年浑浊不动、黄绿色的那汪水默默陪伴夜归的她。舅舅考上了胶州师范。看着录取通知书,母亲开心地笑了,笑容里荡漾着对舅舅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冀。
父母结婚后,我们姐妹四人相继出生、上学。生活无论如何窘迫,我们的学费从来不拖不欠。父亲病逝时,大姐、三姐、我都在求学。村里很多人建议母亲让我们辍学,好早点帮着下地干活。末了加上句:反正是女孩子,读书也没用。对此,母亲总是温和而坚定地回答:只要孩子愿意读书,再苦再难,我都供应。母亲的话拦住了想继续劝阻的人,推动了我们仨吃上“国家粮”的步伐。
母亲不“知书”却“达礼”。踏上工作岗位前,母亲反复跟我们强调上班三项纪律:一是不准迟到;二是不准拿公家一分一毫东西;三是与同事友好相处。母亲的絮叨像一盏启明灯,照亮我们的心胸,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母亲义务当我们的工作纪律监督员,一当就到了我们近退休时。母亲礼数的核心始终是先人后己。我小时候,叔伯大爷家孩子多,粮食不够吃。每年新麦子刚晒干,母亲就推两袋过去,说家里地方窄,临时帮着放放,她的满脸谢意让大爷大娘忙不迭找地方。奶奶在我们家住时,母亲总把白面馒头和菜中仅有的几片肉盛给她吃,自己永远吃最不好看、最没滋味、最凉的饭食,惹得奶奶总说母亲傻。
母亲不傻。70岁之前,母亲一直帮我们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经常去附近小超市买果蔬。等称完重,母亲也算好了账,连年轻的收银员都不得不佩服她口算的速度和准确性。偶尔收银员算错一次,母亲便耐心和她核对,直到无误才离开。
母亲拒绝接受我们赠送的礼物。无论是生日还是过节,送给母亲礼物时,母亲的第一句话永远是:多少钱?如果是衣服,她会责令立即退回,这让我们无数次尴尬又无数次和她争执,最终却总是母亲胜出。是母亲的理论占了上风: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她说,过日子要细水长流,如果平日里不算计花钱,有朝一日就会被钱难倒。
母亲年纪大了,严重的膝关节炎让她无法外出,越来越重的眼疾让她再也无法做缝补衣服的活计。我们上班后,就剩下她一个人孤独地待在家里。为了打发寂寞难熬的时光,除了躺在床上呆呆地看会天棚,母亲有时会拿起剪刀剪纸,各色窗花经她不断变幻的手势扑棱扑棱跳到桌子上,像极了要飞的模样。有时她会找来废纸用反面写字,写得都是我们姐妹四人和五个外甥女的名字。每个人的名字都写得足够大,笔画看上去生疏、夸张,但能读出母亲下笔时的认真。提笔写字的母亲时而微笑,时而黯然,时而喃喃自语,时而缄默不语,笔下的名字便带着她的种种情感一笔笔跳落到纸上,如同一个个鲜活的生灵。母亲啊,想您在写每个人的名字时,脑海里浮现的一定是念念不忘的流金岁月。
我的母亲,虽然您没读过书,但您的认知,您的为人处事,您的言传身教,您的克己向上,您对孤独的接受,您对病痛的隐忍,您对家庭的付出,您对我们的爱,俨然就是文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