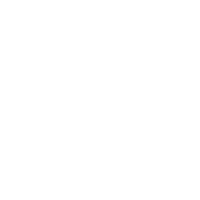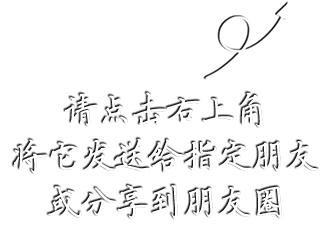灶火正旺
今日高密
2024年12月10日

单立文
霜降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是秋季到冬季的过渡,意味着即将进入冬天,天气渐寒。
今年霜降前一天,高密适逢下了一场小雨,一时秋风瑟瑟。加之昼夜温差更大,早晚天气较冷,就想起了儿时清贫的岁月里,烤灶火,暖心窝。
傍晚,彤彤的灶火映照着祖母手里一个刚从锅灶里掏出来烧熟的鲜玉米棒子。祖母看见我放学回家,就轻声呼唤我:“快来烤一烤灶火,暖一暖身子,吃烧熟的玉米棒子。”
我把烧熟的玉米棒子磕掉灶灰,扒下粒子,塞到嘴里,香甜的味道氤氲,充溢着寒冷的夜晚,带着寒气的身上顿时热乎起来。
儿时的记忆里,农村家家户户都是土锅台,睡土炕,一大家人用一口大锅煮饭,正所谓“一个锅里搅勺子——勺子哪能不碰锅沿儿?”暖暖的灶火,锅台上热气腾腾,拉风箱的“咕哒”声,如同行军埋锅造饭的号角,至今没齿不忘。
木制的风箱又大又长,里面中空,只有两根拴着鸡毛的拉杆,外面则是一个牵拉把手。
我放学回家,总见到祖母一手拿着铲子,一手拉着风箱。锅灶里的柴火草熊熊燃烧,灶火正旺。
那时候,一日三餐,家家户户都在“咕哒”声中,引诱着大人、孩子归心似箭、回家吃饭的步伐。
秋晨,祖母总是第一个起床,点燃灶火,开始一天的生计。我常趴在窗户上看炊烟从屋檐下的烟囱里升腾,袅袅娜娜地在空中飘散,被天空稀释干净。就如同割草口渴,到河边喝水,先往河水里吐一口唾沫,唾沫迅速被水化开、消融,确认是甜水,然后猛灌一气。
祖母做熟早饭,父母到地里做完早工,正好回家吃早饭。祖母便把我们兄弟从暖烘烘的被窝里叫起来,吃完饭,一起去上学。
下午放学,正想放下书包往外跑,小伙伴们正在胡同里等我一起做游戏呢。祖母赶紧叫住我,让我帮助拉风箱,做晚饭。
我很不情愿地坐在锅灶前,许是“馋猫鼻子尖”,我闻到了锅灶里的烤红薯味道,顿时心花怒放,起劲地拉起了风箱,灶火旺旺。
原来祖母事先在锅灶里埋进了几个红薯,让我吃小灶。等饭做好,红薯也就熟了,红瓤烤地瓜趁热吃最是香甜。
有时放学后,我被小伙伴中途拉住,聚堆在街巷玩耍,直到有小伙伴的母亲高声喊叫回家吃饭,我才赶紧溜回家。
祖母已做好晚饭,正把没烧完的木柴从锅灶里拿出来,用水浇灭,留待下次做饭再用。锅灶里余火依然彤红,祖母就把几个芋头埋到火堆里,让余火把芋头煨熟。
每当我急不可耐地催促祖母快点把芋头扒出来,祖母总是笑着说再等等。烤熟后的芋头外皮黑糊,扒开黑皮,雪白的清香扑鼻而来。咬下一口,软软的、滑滑的、甜津津,那股清香味余韵袅袅,至今还萦绕在脑海里。
“真的,我再也没有吃到过那夜似的好豆,也不再看到那夜似的好戏了”,上初中读到鲁迅先生的《社戏》,情不自禁大呼“英雄所见略同”!
不上学的日子,我喜欢看祖母烧火做饭。静静地坐在锅灶旁,看着跳动的火苗红中带蓝,时而又变幻成橘黄色,轻柔地扭着,直到把我的脸颊烤得通红滚烫。
我喜欢那时的灶火,看着祖母忙里忙外,一会添水,一会炒菜。我喜欢喝祖母做的咸汤,把水舀子里的细面(麦子面)粉添加点水,用筷子搅成团粒,慢慢下进烧开的大锅水里,煮成疙瘩汤,鲜咸得当,“味美如啖蔗”。
我时不时把小手放在锅灶口上烤一烤,暖暖手,有时还会把鞋子也脱了,烤烤脚烤烤鞋。嘴里念叨着“烤烤手,写字优。烤烤脚,跑步好。”旺旺的火焰轻舔锅底,心也就跟着暖和起来。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而今,乡下老家的锅灶都换成了液化气,曾经锅灶飘炊烟的场景成为一种历史符号。
随着岁月的流逝,祖母做饭的身影和正旺的灶火反而愈加清晰地回荡在我的心里,浮现在一个又一个漫漫长夜的睡梦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