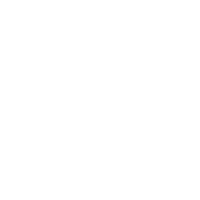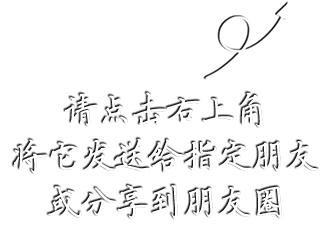明洪武二年大淹山东考
今日高密
2025年05月01日
綦丹喜
(一)
相传,明洪武二年(1369)农历七月一天晚间,胶州知县携幼子到县城古砚大街看大戏,开演不久,孩子哭闹不止,知县极力哄劝,愈哄愈烈,无奈怒而抱其出场,斥其因,子说:“看到唱戏者皆鱼鳖虾蟹,恐惧之极而哭”。说话间,知县顿感地动山摇,继而狂风大作,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暴雨滂沱,远眺南海,似倒海翻江,巨浪滔天,知县突感有大事发生,急回家,跨马挥鞭朝西北大路狂奔,偶回首,看到排山倒海的巨浪紧紧追赶。天渐亮,潍县城隐约可见,知县边跑边喊:“快开城门,洪水来了”!城门打开,策马进城,连人带马瘫痪在地。城里人一看洪水真的来了,赶紧把大门掩上。据说当时洪水只淹到潍县城,至今胶东地区流传着:“洪武二年发大水,胶州莱州亲了嘴,一天两淹两目山,淹到潍县城东关”。平度市东北40公里祝沟镇西北7.5公里有一座海拔417米的两目山,两山峰比肩而立,“群峭立尊,巍然大观”,是当地名山,这次洪水一天淹没两次,故称两没山。当时渤海湾的船只,随水漂至此,至今还有船锚遗留山石夹缝中,山上并有大量的海螺贝壳等。洪水致胶州湾畔古老的洪州城淹没,红岛、上马一带至今有“沉了洪州,立了胶州”的传说,老人们对此深信不疑,有的说祖先来此立村时,这里有座洪州城,附近的程哥庄就是因为立于城后面,开始叫城后庄,后演化为程哥庄。有的说前些年挖土时,还挖出古代盔甲兵器,那就是洪州城的遗物,言之凿凿。五莲县五莲山庙院内有个小石山,呈上下两色,传说下半截被此次洪水所浸,色深明显,两色中间有棵茶叶树,虽死犹存,当年洪水就淹至此。
这次洪水,高密也是重灾区,至今还流传“洪武二年大淹山东,梓童庙上挂浮柴,古城岭上瓜皮水,城西老木田一老头卖土救出六户人家”等传说。高密城东岭梓童庙,建于元代,相传元时乳山赶考举子梓童走至此,突然乌云密布,大雨如注,梓童撑伞,倾刻雨停路干,照常西行,人疑为神,县令建庙祭祀,果连年风调雨顺,香火旺盛。在此之前此地原有一座文昌帝君庙,因同为主宰功名利禄之神,人们亦称梓童庙。此庙坐落在高密八景之一“长陵春色”脊部,是高密城区最高点,海拔56.9米,相传当年洪水就淹到这里,岭顶似露非露,阻挡一些漂流而来的柴禾,庙墙上有一道明显的水浸印记,老和尚常指给香客们看,此庙1947年第三次解放高密时毁于战火。高密城西古城岭,春秋为夷维邑治所,西汉置夷安县,唐武德六年高密县治移至此,洪水高峰时淹没岭顶,水深瓜皮。城西老木田,位于城西北三公里,本为北宋年间从陇西迁来汉飞将军李广后裔李氏之茔地,原为老墓前,元末明初,村中有个李员外,乐善好施,常在各寺庙施舍,周济穷困之人。一日,李员外照例黎明即起,漫步街头,忽见一褴褛老者挑担蹒跚而至,蓬头垢面,面黄饥瘦,口喊“卖土”,李员外一听心生好奇,又觉可怜,忙上前询问:“敢问为何卖土”?老者头不抬地说:“实在饿极,又无资财可卖,只好卖土”。李员外忙道:“请到寒舍用饭”。说罢,引其来至李府,吩咐做饭,来人也不客套,坐下狼吞虎咽,吃饱后站起说:“我所卖之土,你务于今晚子时人脚定后,撒于庭院周围”,说罢,把两筐看似平常之土交于员外,飘然而去。李员外暗忖,看来此土非同寻常,必当按其所嘱,但又想如有用途,怎么能只顾我一家,便于子时悄悄将土撒于庄围子墙上一圈。是夜,沉雷轰鸣,大雨倾盆,汹涌的洪水铺天盖地而来,但李家庄围子墙却神奇地随水流涨高而长高,大水始终没漫过围子墙。就这样李家庄六户李姓人家躲过这场灾难,更名“陆家庄”,后演老墓田,1951年改为老木天,1990年变为老木田,即至今民间所称的“老木天李”。姜庄镇李仙庄,相传隋代此处就有村落,主宰黑龙江的黑龙“没尾巴老李”,其母李仙姑在此住过,死后葬于村东北角,故名李氏仙姑庄,后简称李仙庄。村中心南北大街长二里,宽15米,元代北首建文昌阁,南首建魁文阁,皆高约20米,阁顶常有年轻者在此赌钱,洪武二年大淹山东是夜,一村妇给其在阁上赌钱的丈夫送饭,刚出门,见洪水由南而北滚滚而至,急爬上阁告知,四五人幸免遇难。类似种种传说,各地尚有许多。
(二)
这次洪水,是以胶州湾一带为中心的黄海海域发生强烈地震,地壳剧烈运动引起海啸,致海水大量涌动,加狂风助推冲向陆地,形成倒灌。洪水东起威海卫,西至潍县城,胶州湾海水与渤海湾相连,半岛大部地区一片汪洋。这突如其来的洪水,夜间汹涌澎湃,咆哮而至,使人猝不及防,无情地吞噬着无数村庄民庐,大量人、物、牲畜被水冲走,田畴稼禾被毁。洪水过后,断壁残墙,人、物罕存,满目苍凉,一片死寂。这是元末以来连年战争、温疫肆虐、灾荒频发,本已人口锐减,田地荒废,饿殍遍野,伤痕累累的半岛人民又以致命一击。面对这残重的现实,朝廷在明初全国大移民中把山东尤半岛地区作为重点,先后多次从全国各地移民至此。据统计,山东地区的村庄71%建于明代,而洪武、建文、永乐年间最高。胶东地区的老人至今走路有倒背手的习惯和大小便称解手的方言,据说这都是移民留下的习俗。高密一带还盛传移民来的人脚小拇指是大小两个指甲盖,土著人高密城西“老木田李”是一个,九十年代初,笔者与该村一李姓人氏谈起,遂脱鞋袜视之,果如此。
明初胶东移民,规模较大的六次,首先主要来自山西。因当时山西人口稠密,生活富足。元末时期,由于元统治者的残酷压迫,加之黄河泛滥,旱蝗灾齐发,民不聊生,各地群雄四起,攻城掠地,峰火连天,人口爆减,全国从宋金时期的1.4亿降至明初时6000万,而山西以太行山为屏障,易守难攻,战火甚少,人口有407万,是河南189万和河北185万的总和还多,山东仅剩38万户126万人,与金代相比减少87%。为了恢复生产,稳定政局,朝廷在全国范围展开大移民,从洪武二年到永乐十五年50年间,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移民十八次,遍布全国18个省,526个县、1230个姓氏,移民1500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开始百姓谁也不愿离开故土,官府就采取强制和哄骗的办法,称愿意移民的在家呆着,不愿意的到洪洞县大槐树下集合,听到这个消息,人们拖家带口纷纷赶至,三天聚集十几万之多,官府反其道而行之,把百姓统统围住,按户四口迁一、六口迁二、八口迁三的比例,强制迁移,并称凡移民者不但给路费,分田地,还给耕牛、种子,免三年赋税。尽如此,又有谁肯骨肉分离?为防止中途逃跑,在每个人小脚指划一刀,用来识别身份和使其逃跑不便,并把他们的手倒背绑着,用绳子连着走,人们难免要上厕所,移民便说你解开我的手,我要上茅房,由于不少移民要到千里之外,甚至万里之遥,要走几个月或一年,久之就说解手。就这样,明初主要向山东移民六次,计70万人。胶东地区的移民,虽来自全国各地,但山西洪洞县占主导,至今还流传“借问老家在哪里,山西洪洞大槐树”。招远县城南赵家庵村,出土一座明建文年间古碑,记载该村谢氏“始祖因水灾奉诏于明洪武二年由山西洪洞县东迁招邑”。高密市醴泉街道康庄社区雷家庄《雷氏族谱》记载:“明初雷氏先祖由山西洪洞县移民发迁至高密西北乡今村址落户”。朝阳街道卣坊村,明初始祖赵氏自山西洪洞县迁此。大牟家镇西郇家村,族谱记载:明洪武年间,始祖郇氏由山西洪洞县城东南30里石泉庄迁来定居。柴沟镇张戈庄《张氏族谱》记载:明洪武年间张氏祖先从山西洪洞棋盘街移民至此。现《高密村庄大典》已注明明代立村时始祖从何迁来的共234个村,其中从山西洪洞、临汾、龙门、榆次等迁来的114个,占49%。
其次云南,即小云南,现云南省祥云县,青岛、烟台、日照等地至今流传:“试问先祖在何处,路人皆知小云南”。清乾隆年间《云南县志》载:“云南县,小云南也”。1918年才改称祥云县,之前叫云南县,民间叫小云南,以区别于大云南。明洪武十四年九月初一,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为南征将军,率兵30万南征云南,共打了白石江、鸟撒、大理三次大战,次年2月23日明军对大理发起总攻,末代大理总管段世投降,统治云南445年的段家王朝结束。大理虽被拿下,但反明斗争仍此起彼伏,尤洱海东部的铁索箐等地。为加强统治,明初在云南设了15个卫,其中大理4个,因系前朝旧部,必重兵布防,这当中的洱海卫就是祥云县,即传说中的小云南,是云南所有卫的总部。在平定云南的战争中,大批前大理政权官员及投降官兵集中到此和鸟撒卫,然后用战争结束撤下来的军队,押解到七千里之外的登州府烟台沿海一带和青州府日照沿海地区,一可补充胶东人口,更重要的是抵御胶东绵延1300公里海岸线日益猖獗的日本倭寇。同时又从全国各地移民100万入滇、贵,实行人口混杂,以绝叛乱之患。至今老人过世还举行朝南送魂回云南的仪式。《蓬莱县志》载:“元末,胶东屡经战乱,百姓多被杀戮,县内人口多为明洪武十五年(1382)和永乐二年(1404)两次由鸟撒卫移来”。该县王格庄《蓬莱王氏谱系》载:“明初乃大量向山东移民,本族来蓬莱始祖王泰、王山、王通、王臬兄弟四人,即系明洪武年间由云南鸟撒卫大柳树下村移民蓬莱县城里乡王家山庄也”。高密市有20多个村立村始祖由云南迁来,柴沟镇袁家庄族谱记载:明初袁姓兄弟自云南鸟撒卫迁来。阚家镇双羊社区陈家山甫族谱记载:明初陈姓始祖由小云南鸟撒卫迁此。以及姜庄镇的王家城子,朝阳街道前疃,柴沟镇葛家庙子,柏城镇夏家沟、郝家庄、朱家集等皆来自云南。
再是,从四川移民。元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明玉珍西征平定巴、蜀、黔、滇等地后,在重庆建立大夏国称帝。1366年明玉珍病逝,其幼子明升继位,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派兵攻打大夏国,明升投降,重庆、四川归明,明升遣往高丽。时值山东半岛沿海一带,海盗猖獗,一些逃亡的明军官兵与日本倭寇勾结,侵扰沿海州县百姓甚重。朱元璋心想,何不把这些降兵降将迁去抵御,既可瓦解原大夏政权的残余势力,又可解倭寇之患。于是,把大夏旧部三万降卒及眷属,由明军押解,从四千里之外迁往胶东以莱州为主的登、莱沿海之地,并建立卫所,为军户,实行军屯,抵御倭寇。据《莱州地名志》记载:莱州1068个村中,有751个四川移民村。招远市724个村中有33个,昌邑县812个村中有129个。莱州虎头崖镇潘家村保留的一份家谱记载:“吾祖故籍四川建昌,明洪武五年,为夏王开帝明升之降卒,移师至京师(南京)、阊门(江苏北门),明弘治二年(1488)复迁至山东莱州,始祖潘士成,为军户,供职于马埠寨;二世潘友亮,生于京师阊门,时年十六岁,当年取本地徐氏为妻,生子潘岗……”。莱州虎头崖镇孙氏家谱记载:“孙氏始祖孙始良,在明永乐二年由四川成都府双流县大柳树村铁碓臼迁来莱郡掖县龙德乡虎头崖镇东宋疃(现东宋村)定居落户……”。高密市明初由四川迁来立村的十六个,井沟镇郑家村家谱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郑氏始祖从四川迁西乡郑公村,又迁柴沟镇东华山,后迁此定居。柴沟镇王家岭王氏,明初由四川泸州兰山县郭步庄迁此。这些移民大多说从四川“铁碓臼”迁来,光平度市就记载有十一个:大泽山镇孙家庄始祖孙一元洪武二年由四川铁碓臼孙家迁来;新河镇三埠村始祖孙禄洪武二年由四川紫阳县大槐树铁碓臼迁来,新河镇西八甲村始祖王天礼、王天福洪武二年由四川对臼王家徙此地等。其实“铁碓臼”是古代军队卫所插旗杆用的形似舂米的臼,是军队卫所的标志物,明军先把移民集中到此,然后再向不同的地方迁移。
据记载,明初移民主要是山西、云南、四川,其次是河北北直隶枣强,河南安阳、荥阳、开封,江南省南直隶、宿迁、海州、南京以及山东的历城、青州、曹州、阳信等地。
(三)
此次洪水,因《明史》《明实录》《明太祖实录》等典籍均无记载,地方史志和族谱亦记载甚少,故在学术界存有两种观点:一种根本没有此事,纯属讹传,这种占主导;一种确有此事,但证据不足。对此,笔者一直心存疑惑:认为650年来,千百万民众一直代代相传,久传不息,绝非无中生有、空穴来风,确有诸多疑点和事实依据值得商磋。
一、为什么流传年代这么久、范围这么广?明初山东设六府,其中登州府、莱州府和青州府日照沿海一带都遭洪水,特别是半岛附近沿海和胶莱河连接的胶州湾与渤海湾地域尤为严重,区域之大、范围之广实属罕见。山东半岛面积7.3万平方公里,其中胶东地区就3万平方公里,加日照、潍坊部分(时潍县、昌邑县属莱州府)地区约4万平方公里,计百万人之众,在交通极不方便、信息极不畅通的明清时期是怎么如约而传的?且传说雷同,如讹传,又是谁为什么去制造这样的虚假谣传?如在当时没有大量确凿的事实根据这么多人会信吗?
二、明代以来,记载胶东洪水海啸多期:《明太祖实录》记:“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正月,山东登莱等府水灾,秋粮宜悉免之”。康熙《济南府志》卷11《灾祥》记:“明嘉靖三十六年(1577)七月初八日,海啸潮南溢八十余里”。又记:“明嘉靖三十七年二月初五日,海啸潮南溢六十里”。《增修胶州县志》记:“明成仪(1471)七年秋闰九月海溢”。《明史》记:“明万历二十三年(1594)胶州大饥,海水溢,稼禾一空”。《平度大事记》记:“明万历十四年(1586)六月大水,平地三尺”。《高密县志》记:“明正德十二年(1517)九月地震、隆庆三年(1569)大水坏民庐,死者无算,夏庄地圻数处,水涌如墨,旋合,十八日复震,七月十七日、八月十八日复震”。康熙四十年(1701)六月二十九日,大雨如注,自午至申,震电昼晦,火光四散,触物皆焦,平地水深数尺等等,对这些有正史记载且极其严重灾害的民间从未听到传说,而对洪武二年大淹山东无正史记载的却广为流传,何因?
三、胶东地区村庄为何多在明代所立?明初前为何所剩无几?1999年山东省地名办公室对山东地名进行调查,编辑出版了《山东省地名志行政区划·居民地卷》,共收录了自然村落6000余,其中根据家谱、方志、以及口承资料,4830个自然村落建村可考,在这当中建于明代的3429个,占总数的71%,而又绝大多数建于明洪武至永乐年间(1368-1424)。莱州市现有资料可考的1042个村,其中明代前立村的仅64个,占6.1%,明代后978个,占93.9%。高密市现有自然村904个,未注明立村时间的30个,立村时间有据可考的874个,其中明代前立村30个,占0.35%,明代后立村844个,占96.5%,这当中明代立村683个占78%(其中明初358个),清代立村161个,占18%。在明代前立村的30个中,永安村北宋李氏所立,姚哥庄村五代鞠氏所立,南曲村宋初曲姓迁此,东牟村原汉高密侯邓禹后裔之墓所在,至宋初乔姓来此,梁尹村金代任福由河南开封来高任县尹,谢任后而定居等。这些明代前立村的,有的因朝代鼎革,岁月变迁,几度兴废,难以考稽。如大周阳相传东汉阳嘉年间管仲后裔分封于此,村落几废,村名未改,然无管姓居住。更应说明的是:许多古老村庄,现居住人全是明初迁入的,而原土著者皆无。朝阳街道仓上村,相传汉代将军王党曾在此屯兵与张鲁交战,营寨北是王党的仓库,故名仓上,明正德年间,汉将军李广之后由柳沟崖迁此,据记载:迁来时村西北200米处有古村落遗址,名为“土庄”,明初被大水淹没夷为平地。柴沟镇城子前,春秋时今村址后有一土城,名诸晏城,隋初置胶西县,因村庄位于胶西城前,故曰城子前,几千年村名延用至今,而今居民为明万历年间迁入。姜庄镇四城子,为汉代胶阳城遗址,自古发达,而今之居民分别为王姓彭姓,于明洪武年间自小云南迁入,秦姓明隆庆年间自安徽凤阳府、栾姓明初于招远黄山馆徙此。夏庄镇綦家村据《诸城县志》载,东汉末年汉献帝刘协之皇后伏寿与娘家父伏完密议诛杀曹操,事泄一家百余口被诛,家乡诸城(时称东武)获悉,一支逃往现綦家村、刘家村之处立村称伏家庄,明永乐年间綦姓始祖綦麟迁来时已是废弃村庄,村名未改,沿用之建国初改綦刘二村。密水街道拒城河村《太平寰宇记》、《齐乘》中记作柜城河,为柳沟河源,汉代就是柜县城,拒城河为柜县城,环城之河,相传春秋时耿姓立村,而今之居民为明初张姓徙来。该街道莳戈庄,元朝以前莳姓立村,明初被洪水吞没,后王氏由济南府长山迁居,仍沿此村名。柏城镇大村,相传春秋齐国时该村已有住户,至明洪武二年南海、北海啸聚水灾,原祖居人家绝灭,遂为平地,洪武六年,朝廷强令由云南迁民至此,据明万历甲辰仲春修《山左宿氏族谱》序:“我宿氏原籍四川嘉定州夹江县人,自明代初始祖兄弟四人应诏播迁山左分地而居……始祖业甫居高密东南乡宿家店子,八世宿党、宿泰大村”。井沟镇城子村,“城”则因周朝“谷稻城”而名,并非“城阴城”之城,“谷稻城”简称“稻城”。历代为屯粮牧马之城,为城阴城之卫星城,西汉时曾为侯国都城,也曾为县之治所,唐后荒废,人们在废城上立村,名城子村,千百年来居住该村的家族迁入迁出,村名一直未改。《山东通志》载:“元末明初,山东沿海州县连年兵荒,时产红头毒蝇,瘟疫大行,逐人成灾。时又东海啸,西至济南南北,距海洼上皆淹,由此十村九空,迨至明洪武二年移民垦田”。这段记载就是高密民间传说中的洪武二年大淹山东和元末大瘟疫。由于明初大水灾、大瘟疫后人口锐减,东依潍河的城子村受灾尤重,原城子村在明初已荒无人烟,可谓货真价实的废都,于是从明朝初年这里不断有外地移民迁入,今城子村民大都是明朝移民的后裔。如今该村第一大家族田姓的《田氏家谱》:“田氏世居济南府阳信县桑乐树村,于明初避红蝇之灾迁居昌乐县治以南申明亭之西北。洪武四年版定田村社,纳赋当差,自此营陵境上有田氏一族矣。……至明正统年间(1436-1450),荣富公由乐迁密,居潍水之东岸城子庄。自明初以来,徙迁崎岖,历经五百六十余年”。
据以上可考的立村时间百分之八九十都在明代以后,其世辈多在二十至二十五世左右,距今约600余年,时间段之集中,涉及面之大,历代少见。更使人匪夷所思是不少县到明初仅剩几十个村庄,可谓所剩无几。是什么原因使胶东人口几近灭绝?主要有四:首先是战争。北宋末来,宋金、宋元、金元和元末农民起义等战争连续不断,此起彼伏,给胶东地区带来巨大创伤。同时胶东本地也战事频发:杨安儿“红袄军”与金、蒙在密、莱、登等地互相争战,李壇反叛蒙军,元末红巾军首领刘福通部将毛贵抗击蒙军,拉锯战在山东打了三年,元至正十七年(1357)攻克密、胶等州,兵燹战火,百姓死亡无数。史籍载:“金季大乱,阻山濒海之薮,盗贼千百为群,啸聚山谷,比猎人以为食,居民苦甚”。民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农田荒芜,食物罕缺,呻吟呼号,卖儿鬻女,盗贼竞比“猎人为食”,荆榛千里,斗米至数十千,且不可得,“人肉之价,贱于大豕”,老瘦男子,廋词谓之饶把火,妇人少艾者名为不羡羊,小儿呼为和骨烂,又通目为两脚羊”。说明当时杀活人食其肉已是常事。战乱造成人烟稀少,民国《牟平县志》载:“查《金地理志》:宁海州辖牟平、文登二县,户六万一千九百三十三。《元地理志》宁海州仍牟平、文登二县,户五千七百一十三,口一万五千七百四十三,是元初户数较金十分之一,而丁口每户不足三人,乱难之后,孑遗无几存”。这样兵连祸结,生灵涂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其次灾害。元末,旱、涝、蝗灾接踵而至,《元史》记:元末山东水、旱灾害就高达18次。光绪《高密县志》载:“顺帝至正三年(1343)地震,四年旱,七年地震,八年大水。胶州史料记载:“至正三年十二月地震,六年春二月地震,七年春二月地震,二十七年五月地震”。各种灾害轮番出现,交差上演,胶东恶殍遍野,死者无数,外逃求生者甚众。再是瘟疫。大灾必有大疫,元末,各种瘟疫多发,尤诸城爆发红头苍蝇,多的铺天盖地,见物就咬,敷食人体及牛羊等牲畜,被叮后即患病死亡,数十日不少村十室九空,且波及山东诸多州县。红头蝇至处,无一逃亡,唯诸城臧家安全无恙,他们把门窗堵好,白天看见进屋就用“蝇摔子”打,夜晚把簸箩扣过来在里面睡,加之在簸箩编好时用硫磺熏白,可能苍蝇怕此味不敢钻入,全家人躲过一劫。清嘉庆年间高密名医刘墉堂兄逄戈庄刘奎所著《松峰说疫》中记:“入夏瘟疫大行,有红头青蝇,千百余头,凡入人家,必有患瘟疫而亡者”。这次大疫又使胶东人口大减。最后洪水。笔者认为,导致元末明初胶东人口骤减、有的县村庄百不剩一二的最终根源是洪武二年地震引发的洪水。夜间洪水汹涌突至,根本不是人类所能抗拒的,因而导致灭顶之灾。除离海较远或村居高处,余无一幸免。在一个面积三四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地区,战争、旱涝、蝗灾、瘟疫地区之间必有轻有重,就人口、村庄减少而言,致伤不致命,然海啸洪水则不然,能对人类造成毁灭性打击。洪水过后,幸存者恐惧之极,谈虎色变,已像惊弓之鸟,多少年代后闻之睹物都心惊肉跳、毛骨悚然,才使此事代代相传,各地虽相隔千百里却异口同声,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确有其事才广为流传。
四、为什么胶东地区的府、县志均无记载?该地的府县志大都始修于明后期,《莱州府志》始修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由大学士毛纪归里后修,后藏于宁波天一阁毁于火灾失传,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知府龙文明重修。《登州府志》始修于明泰昌年间(1620),《莱阳县志》始修于明万历八年(1580)、《高密县志》始修于明万历二十三年(1605),《潍县志》始修于明万历元年(1573),《黄县县志》始修于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昌邑县志》始修于明万历五年(1577),《即墨县志》始修于明万历七年(1579),《海阳县志》始修于清乾隆六年(1741)等,距洪武二年200年许,且始修志多被失传。200年年深代远,沧桑巨变,物是人非,当年的情景已成为尘封的历史,遥远的过去,难以为据,各地邑志又如何记载?再是胶东各地族谱,除个别名门望族创修于清代前,民间多始修于清初,兴盛于清后期道光年间,时已过洪武二年四五百年,且明初后移民,皆无亲身经历此次洪水,只是听说,无根无据,怎么记载?恐《明史》、《明实录》等正史之所以未记载,与明刚立国,战事仍频,灾害犹重,朝纲正立,百业待兴,史料记载尚不完善有关。
五、为什么胶东一带明初前的文史资料断代缺失如此严重?多数事件自明正德万历年间起有记载,之前多来自国家史籍和本地出土文物及碑记,这是不争的事实。那么明初前为什么文史资料少?究其原因,除宋“靖康之耻”后胶东大部世家望族随赵构南渡避难,如诸城的赵明诚、李清照,高密鞠常、綦崇礼、侯蒙等家族南迁时大量资料带走,金、元统治对我华夏文化的糟蹋和战乱损失外,恐与洪武二年毁于洪水不无关系。
总之,笔者认为:洪武二年大淹山东不是讹传,而是确有其事,只不过不是像传说的那么严重而已,且《山东通志》和各地村史、族谱均有记载已为证。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迹的挖掘、信息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会进一步揭开这尘封的泥土,还历史以本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