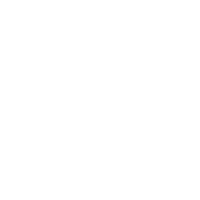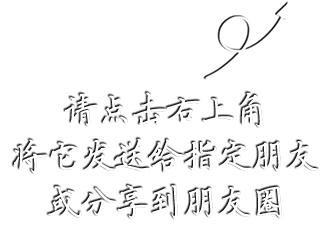说说我和莫言的故事
今日高密
2025年12月25日
◎崔志亮
若说莫言的故事在家乡满天飞,有些夸张;若说莫言的故事在家乡不是满天飞,又让人不相信。正好今天闲暇,就想和大家说说我和莫言的故事,不是为了攀附名人,只是因为感觉有这么一位文学界的大咖做老乡,特别自豪。
家乡出了位作家莫言,对我这般的文学爱好者而言,更是与有荣焉。心里像揣了只活蹦乱跳的兔子,恨自己没长翅膀,立刻飞到莫言身边,去请教那些在胸腔里发酵了许久的文学问题,去聆听那想象中的、春风化雨般的谆谆教诲。
这念头的种子,怕是早年就埋下了。我的高中语文老师单亦敏先生,和莫言是邻居。单老师曾笑眯眯地回忆,莫言小时候常到他家串门子,有一次,他告诉那个黑瘦的、眼睛格外亮的孩子:“济南一位大作家,每天能吃三顿饺子。”就为这“三顿饺子”,莫言立下了鸿图大志。后来,另一位语文老师王兆勤先生,又用赞叹的语气告诉我,莫言的小说《民间音乐》受到了孙犁先生的首肯。孙犁啊,那名字本身就闪着光。连我的邻居,河崖公社轧钢厂的会计郭士勤大叔,一位文学爱好者,有一次我去他家,他正捧着《收获》杂志读莫言的《球状闪电》,读得入神。见我来了,他摘下老花镜,很认真地对我说:“孩子,你得向莫言学习,先立志冲出咱这地方,再想着回来造福家乡。”
这些话,像细雨,无声地渗进我心里那块向往文学的薄田。
1985年,我考上了山师大中文系。同学们知道了我和莫言是老乡,那份热切便找到了出口。他们鼓励我走创作的路,更有那心直口快的,拍着我肩膀说:“赶超他!”我哪有那么大的志向和天赋?只是心里那点火星,被扇得更旺了些。那时,我也偷偷鼓捣点“豆腐块”文章,加入了系里的“绿原文学社”,工工整整地抄了稿子,贴在橱窗里,下一期眼巴巴等着看有没有几句点评。仿佛那橱窗就是通向文学世界的第一个窄门。
也正是在那时,我第一次系统读到了莫言。《透明的红萝卜》里那种通感的、疼痛又瑰丽的想象,《红高粱》中那股泼辣粗粝、酒神般奔涌的生命力,让我彻底呆了。读罢,不是激动,而是一种深重的自惭形秽,感觉自己那点小心翼翼的描摹,离那片土地真实的、滚烫的魂魄,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系里为此搞了一次莫言作品研讨会,赞美声如潮,可也夹杂着些质疑的礁石。我的恩师宋遂良先生,一面为莫言天马行空、汪洋恣肆的才情击节赞叹,一面又对他某些“不加节制”的描写,微微蹙眉,颇有微词。我曾模仿莫言那泥沙俱下的语言风格,写了一篇《一捆秫秸》,兴冲冲拿去请宋老师指教。老师看了,沉默片刻,然后毫不客气地“枪毙”了。他说:“学他,不是学皮相。你还没找到自己的声音。”一盆冷水浇下来,我那股盲目的创作热情,连烟都熄了,只剩下一地冰凉的灰烬。大二期间,我还给莫言写过一封信,莫言没有专门为我回信;他在给我的恩师杨守森先生的复信中转达了对我的鼓励。
然而,想见莫言一面的渴望,却在那灰烬底下阴燃着,不曾熄灭。
机会来得突然。1987年暑假,空气里满是泥土被晒透的香气。表兄来我家,说电影《红高粱》要开拍了,莫言回了老家。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吃过午饭,表兄骑上他那辆“大金鹿”回大栏乡,我二话没说,推出父亲的自行车,跟了上去。一路上,风在耳边呼呼地响,路边的白杨树叶哗啦啦地翻着银白的背面,我的心也像那叶子,慌乱地翻腾着。
进了高密东北乡那片熟悉的村落,拐进那条土巷,推开那扇普通的木门,莫言,竟然真的就在家里。院子敞亮,地上晒着些豆秸,散发出好闻的植物气味。莫言的大哥管谟贤校长也在,他刚从湖南调回高密一中任副校长。我们就在院子里,围着一张矮矮的饭桌,坐在小马扎上。莫言的母亲,一位慈祥清瘦的老人,忙着用柴火烧水。大哥则用一把老旧的提梁壶,给我们沏茶。茶是普通的茉莉花茶,但那股香气在乡间的院子里飘散开来,竟有一种别样的安宁。
我有些拘谨,问大哥为什么从湖南调回来。大哥啜了口茶,笑着说:“那边冬天没暖气,湿冷,那冷气啊,像是能绕过皮肉,直接钻到骨头缝里去,北方人受不住。”莫言话不多,听着我们聊,目光有些散淡地望着院子角落。我鼓起勇气,问起创作的事。他转过头,语气平和,像在说一件最普通不过的道理:“不必光读我的东西。古今中外,好的都要读。甚至,非文学的书,历史、哲学、杂学,更要读。”他说这话时,并没有看着我,他的目光,落在他母亲赊来的一群半大的鸡雏上。
那群鸡仔正在地上啄食撒开的高粱米。一只小公鸡,羽毛刚刚显出些鲜亮的颜色,脖颈昂着,十分强梁。它不许任何一只小母鸡靠近食物,谁敢上前,它便梗着脖子,竖起颈毛,凶狠地啄过去。小母鸡们惊惶地躲闪,咯咯低鸣,敢怒不敢言,只能围在外圈,眼睁睁看着那“霸王”独享美餐。
我们都看着这场景。忽然,不知何时,莫言的手里多了一根柔韧的棉槐条子。说时迟那时快,他手臂轻轻一扬,那枝条在空中掠过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虚影,“啪”一声轻响,正抽在小公鸡昂然的头颅上。
小公鸡一下子懵了。它停止了啄食,晃了晃脑袋,似乎不明白发生了什么。接着,它开始踉跄,脚像踩在棉花上,脖子软软地耷拉下去,又颤颤巍巍地想抬起来。它歪歪斜斜地转着圈子,每转半圈,便无意识地往空中啄一下,眼神涣散,模样既滑稽又可怜。
“看,”莫言放下枝条,嘴角浮起一丝孩子般的、恶作剧得逞似的笑意,“脑震荡了吧。”然后,他收敛了笑容,看着那群终于敢试探着围上来啄食的小母鸡,轻轻说了一句:“我最看不惯以强凌弱。”
那一刻,院子里忽然很静。只有母鸡们安稳啄食的“笃笃”声,和那只晕头转向的小公鸡偶尔发出的、含糊的“咕咕”声。午后的阳光明亮地泼洒下来,照着他平静的侧脸,照着他母亲含笑的眼睛,照着一地金黄的粮食和终于得以共享这份安宁的鸡群。我望着他,忽然觉得,之前读过他所有的文字,那些辉煌的、狰狞的、浓墨重彩的篇章,仿佛都在这一刻,被这轻轻的一句话,这道迅疾而精准的弧光,照透了,点亮了。它不是来自书斋的哲学思辨,而是从土地里长出来的、最朴素的正义,是一个沉默的观察者,对生命之间那微妙平衡的本能守护。
什么时候告辞的,如何告的辞,三十八年白云苍狗,弹指一挥间,记忆早已漫漶不清。唯有这个故事,这个午后院子里微不足道的插曲,却像用那根棉槐条子,抽打在我心版上的一道印记,清晰,深刻,永不磨灭。我从那时起才懵懂地觉得,自己似乎触摸到了他那“作为平民写作”的胸膛里,跳动着一颗怎样的心。那不是俯瞰众生的悲悯,而是置身其中的体温;不是声嘶力竭的呐喊,而是随手为之的、近乎本能的“看不惯”。
后来,我终究没有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那棵参天大树撒下的荫凉太广袤,他长出的方向也太独特,让我这株小草,看清了自己更适合在平凡的泥土里,汲取另外的露水与阳光。但那次仰望,却成了我精神世界里一枚永久的坐标。它让我懂得,真正的力量,有时并非轰轰烈烈开疆拓土,而是能在某个寂静的午后,为一个微弱的、被欺凌的“咯咯”声,毫不犹豫地扬起手中柔韧的枝条。
这,就是我与莫言老师仅有的一次见面。我把它说成是一株小草对一棵参天大树的仰望,想来,是可以的吧。树有树的凌云之姿,草有草的匍地之情。而那片我们共同扎根的厚土,因了那一下精准而温柔的抽打,在我记忆的天空下,永远回荡着一声关乎正义的、清亮的回响。